注意力经济与越发难以集中的人们
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网络上的精彩内容层出不穷,但自己却很难集中注意力去仔细阅读信息。这种情况可能并不特殊,在过去20年间,人类的平均注意力持续时间集体下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信息学教授格洛丽亚·马克(Gloria Mark)表示,人们集中在单一屏幕的平均关注时间从2004年的2.5分钟下降到2021年的平均47秒。
人们注意力的集体下降并不新鲜,早在2015年,微软在一项针对2000人的研究中发现,自2000年移动革命兴起以来,人们的平均注意力持续时间从12秒下降到了8秒,显示出日益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对大脑造成的影响。研究者发现,“频繁使用多个屏幕阅读信息的人,很难过滤掉多方的刺激。他们更容易被不同媒体分散注意力。”报告指出,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移动时代,我们的多线程任务处理能力大大提高了。微软推测,这些变化是由于大脑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适应和改变自身的结果,而注意力持续时间变弱可能是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副作用。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所谓的注意力下降现象是由我们选择的比较对象所决定的。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的艾玛·史密斯教授指出:“将我们的注意力与理想化的过去进行比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们的注意力始终是由更广泛的背景所决定的。影响我们的不仅仅是智能手机。每一项新技术,从最早的书籍到便携式钟表,再到眼镜和火车,都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理解和互动方式。”
史密斯教授提出,在工业革命期间,专注代表工作纪律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E.P.汤普森用“专注”(concentration)来描述新型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打卡制度。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工厂或纺织厂中,“专注”意味着扮演一位默默顺从的“好工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分心不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对内化的清教徒工作伦理的一种激进的反抗。
与之相对,今天被许多人所褒奖的“在阅读中的沉浸式专注”也并非天生的自然行为;而是后天习得,它由当时的“新媒体”促成,在特定的历史和技术环境下产生。就像当下的数字化时代的分心一样,深度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特定新技术(小说)的产物。讽刺的是,在小说刚出现时,深度、沉浸式阅读并未被视为极富专注力的表现。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将易受影响的读者与现实世界割裂开来的方式,可能对读者的姿势、视力和道德产生不利影响。
史密斯教授总结道:我们需要在历史视角下,看待当下的分心现象。专注是一种社会化、后天习得的行为。现代人对观看整季电视剧和收听多集播客的热情表明,我们并没有失去专注的能力,而是将它引导到了不同的媒体上。
或许注意力的确受到不同时代、社会、技术的影响,但当下社会对于注意力的关注与商品化却是前所未有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格雷厄姆·伯内特(D. Graham Burnett)认为:市场将人类的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展开“注意力经济”的竞争,为我们的注意力定价。这种经济正在影响着互联网、社交网络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注意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货币化,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淘金热,某种巨大的、技术密集型、高度资本化的项目,正在对我们最私密和基本的注意力进行剥削,以获取利益。伯内特将该过程描述为人为压裂,他说,这种对我们注意力的竞争是有害的,它“动摇、污染并破坏了人们存在和人与人关系的实际结构”。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 )在1971年提出了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并指出了信息过载和注意力缺乏之间的联系,他写道:“信息的丰富会导致注意力的缺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戈德哈伯(Michael Goldhaber)等作家对注意力经济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获得注意力就是获得一种持久的财富,它使你处于有利位置,可以获得这个新经济所提供的任何东西。”
现在,注意力经济已经获得了更为具象的体现。《福布斯》杂志写道:每一次滚动、点击、点赞和分享都不仅仅是一个动作;而是一次关于我们注意力的交易。仅在2023年,全球净广告收入就达到了惊人的8530亿美元,这一点最能体现注意力的价值——如果他们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他们能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公司对于注意力资源的追求,伴随着算法的针对性吸引,以及不断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哈佛商学院的名誉退休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将这种行为称作“监控资本主义”,即收集你的数据,追踪和预测你的行为。此外,视频网站的倍速播放,社交网站对于输入内容的字数限制,越来越多的快速剪辑都是吸引注意力的尝试——平台的最终目的是让用户继续滚动页面,以延长他们在网站上的停留时间。
在这种环境下,利用好我们有限的注意力变得更为重要。格洛丽亚·马克教授给出了以下建议:制定好休息计划:避免倦怠,通过冥想、散步或阅读一些鼓舞人心的东西来恢复精力;放下手机,逐渐增加没有手机的时间,记录自己使用社交平台的时间;了解自己每天注意力的高峰和低谷,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对自己的行为建立意识,不要让使用手机成为下意识的行为。
在所有相关的报道和研究中,《福布斯》杂志作者柯特·斯坦霍斯特(Curt Steinhorst )的视角或许最为贴近我们的生活。斯坦霍斯特写道:当我和我的妻子同时打开社交媒体,我们所接收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即使我们并肩而坐,数字体验也在推动孤立和疏离。我们的注意力被不同的信息占据,而我们的共享体验却在减少。注意力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量身定制的世界,根据偏好和兴趣呈现给我们精彩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它威胁着我们注意力的质量、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恰恰是注意力的本质: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项活动上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忽略了无数其他活动——这些选择描绘了我们生活的轮廓,塑造了我们的人际关系、知识、健康和幸福。
融化的大脑
8月13日,环境新闻网站 Grist 的数据记者Clayton Page Aldern在Aeon网站刊文介绍了环境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研究揭示,气候变暖的影响已深入到我们大脑皮层的沟裂中。Aldern是一位由神经科学家转型为环境记者的专业人士,著有《自然的重量:气候变化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202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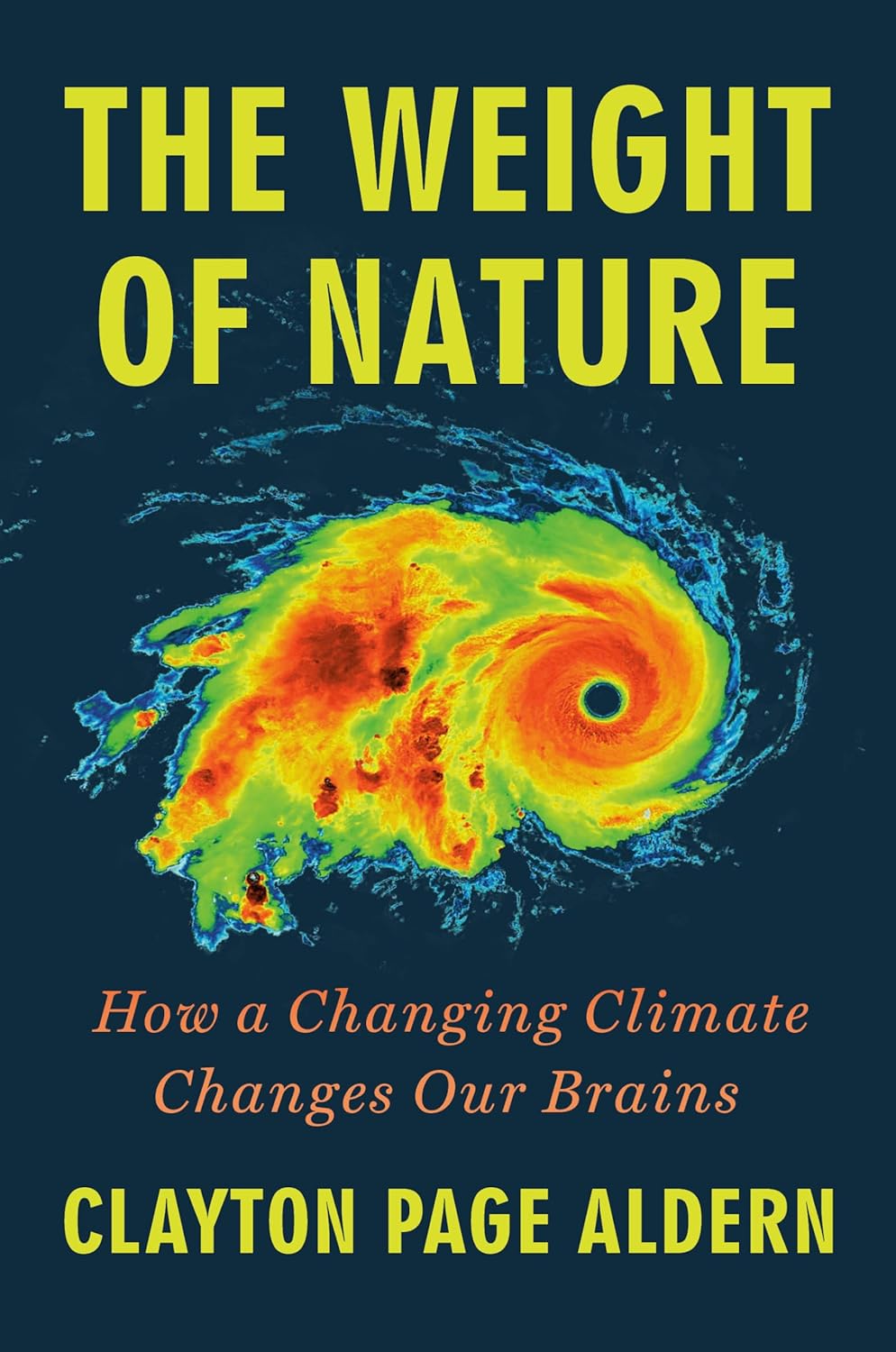
《自然的重量:气候变化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2024年出版)书封
1884年,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伦敦学会发表演讲,描述了一种新出现的“瘟疫云”(plague-clouds)现象,并将其与社会的“道德阴霾”联系起来。拉斯金的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他后来确实经历了精神崩溃,晚年被认为是疯了。
然而,拉斯金的观察实际上反映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变化。他认为这些“瘟疫云”是工业化的产物,代表了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迁。拉斯金提出了环境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认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也会损害人们的心理健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新颖的想法,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当前的气候变化与一个多世纪前拉斯金所描述的“瘟疫云”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规模和影响更为广泛,气候变化还可能影响人类的内在心理和行为。研究表明,高温天气与一系列负面行为和结果相关,包括:移民法官做出不利裁决的可能性增加、学生学习表现下降、网络仇恨言论增加、家庭暴力和自杀率上升等。
日常生活中,人们在高温天气下可能会感到更易怒、思维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科学研究支持这些观察,如高温天气下司机更频繁地按喇叭,运动员更具攻击性等。
这些现象表明,环境(特别是温度)对人类行为和决策过程的影响,比我们直觉认为的更加显著。这种影响突显了人类行为能力的脆弱性,以及我们内在世界与外在环境的密切联系。
文章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气候变化对神经系统的可见影响。2024年5月,24位主要来自英国的临床神经学家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论证全球变暖可能影响“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流行率和严重程度”。
在他们对332项科学研究的综述中,大脑正在成为气候变化最脆弱的景观之一。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偏头痛、中风、癫痫和多发性硬化症等。
气候变化还可能增加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如精神分裂症、自我伤害和其他心理健康障碍。气候变化导致的病媒范围扩大,可能增加脑部疾病的发病率。环境变化影响感官系统和感知,可能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如ALS、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妊娠期高温暴露可能增加后代患神经精神疾病的风险。高温可能影响大脑功能,如改变功能性脑网络、影响前额叶皮层活动、引发神经炎症等。
新兴的环境神经科学领域致力于研究外部环境与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正在萌芽的、综合性的领域,可称为气候神经流行病学(climatological neuroepidemiology)。
文章作者提出“自然的重量”这一概念,用来描述气候变化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强制性影响。这种“重量”限制了人类的选择,例如极端高温可能导致人更倾向于暴力行为。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的决策过程,可能减少深思熟虑的决策,增加冲动决策,从而损害我们感知到的自由意志。作者认为这种影响是沉重的,会使人感到错位。
将神经生物学导向气候变化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文章进而点出将神经科学应用于气候变化研究和应对策略的潜力。
自拉斯金对着天空挥舞拳头以来的几十年里,环境神经科学已经开始探索生物体与其生态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现在知道,现代环境的纹理——绿地、城市扩张、社会经济阶层——都在大脑上留下了印记。气候变化也不例外。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神经科学家Kimberly Doell及其同事认为,科学家和倡导者都可以整合神经科学的发现,以改善旨在促进气候行动的沟通策略。他们想要扭转局面,利用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见解来更有效地设计气候解决方案——既针对我们自身,也针对整个社会。
例如,贫困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将社会经济条件与不佳的健康状况联系在一起。近年来,神经科学已经逆向工程解析了贫困的各种伤害——刺激不足、有毒暴露、慢性压力——如何侵蚀神经结构并破坏认知发展的途径。仅靠脑科学无法解决贫困问题,但即使对这些机制有限的理解也推动了诸如Head Start等项目的研究,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学前教育课程,已被证明可以提高选择性注意力(在电生理记录中可见)和认知测试分数。尽管结构性不平等这个九头蛇不易被杀死,但神经科学家已经成功地揭示了贫困的神经相关性,标记了其可逆的危害,并据此设计了精确的补救措施。Doell和她的同事认为,这种潜力同样适用于气候变化的神经科学研究。
要实现这种潜力,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人类世的噩梦般景象如何已经扭曲了我们的大脑。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已经开始记录地球变化带来的心理影响,但气候变化的神经分类学还有待建立。该领域的方法论和概念武器已经为这一挑战做好准备,但要磨砺它们需要与气候科学、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共同努力。
美国洛杉矶的卡夫里基金会(Kavli Foundation)提供资金支持研究神经系统如何对生态剧变做出反应,重点关注大脑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研究项目涉及多种生物,如甲壳类动物、头足类动物和斑马鱼,以了解它们在面对环境变化时的神经适应机制。2023年11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探究神经生理学对人为环境影响的反应机制。
作者认为,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已经显示出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迹象。
我们现在知道,大脑与其说是一块静态的自我调节组织,不如说是一个动态的、活生生的景观,其山丘和谷地由我们的环境轮廓塑造。
但大脑与生物圈之间的对话并非单向。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追求的行为,我们在危机世界中导航的方式——所有这些决定都会反映到环境中,无论是好是坏。因此,作者提出:在寻求理解变化的气候如何塑造我们思维的轮廓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为了可持续性而改造我们思想的架构。
文章最后引用拉斯金的话说:“消除不完美就是摧毁表达,阻碍努力,使生命力瘫痪。”(To banish imperfection is to destroy expression, to check exertion, to paralyse vitality.)即使我们也许有能力,我们也不应该消除环境对心灵影响所谓的不完美。相反,我们应该在其中读出自我与世界之间亲密而重要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气候学神经流行病学——尽管它可能还很年轻且未经检验——正准备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在凝视气候改变的思维这个黑匣子时,在阐明我们行星困境的神经回路时,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在一个常常感觉失控的世界中,它给予了一丝主动权的闪光。它暗示,即使自然的重量向我们压来,我们或许仍能找到反击的方法。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